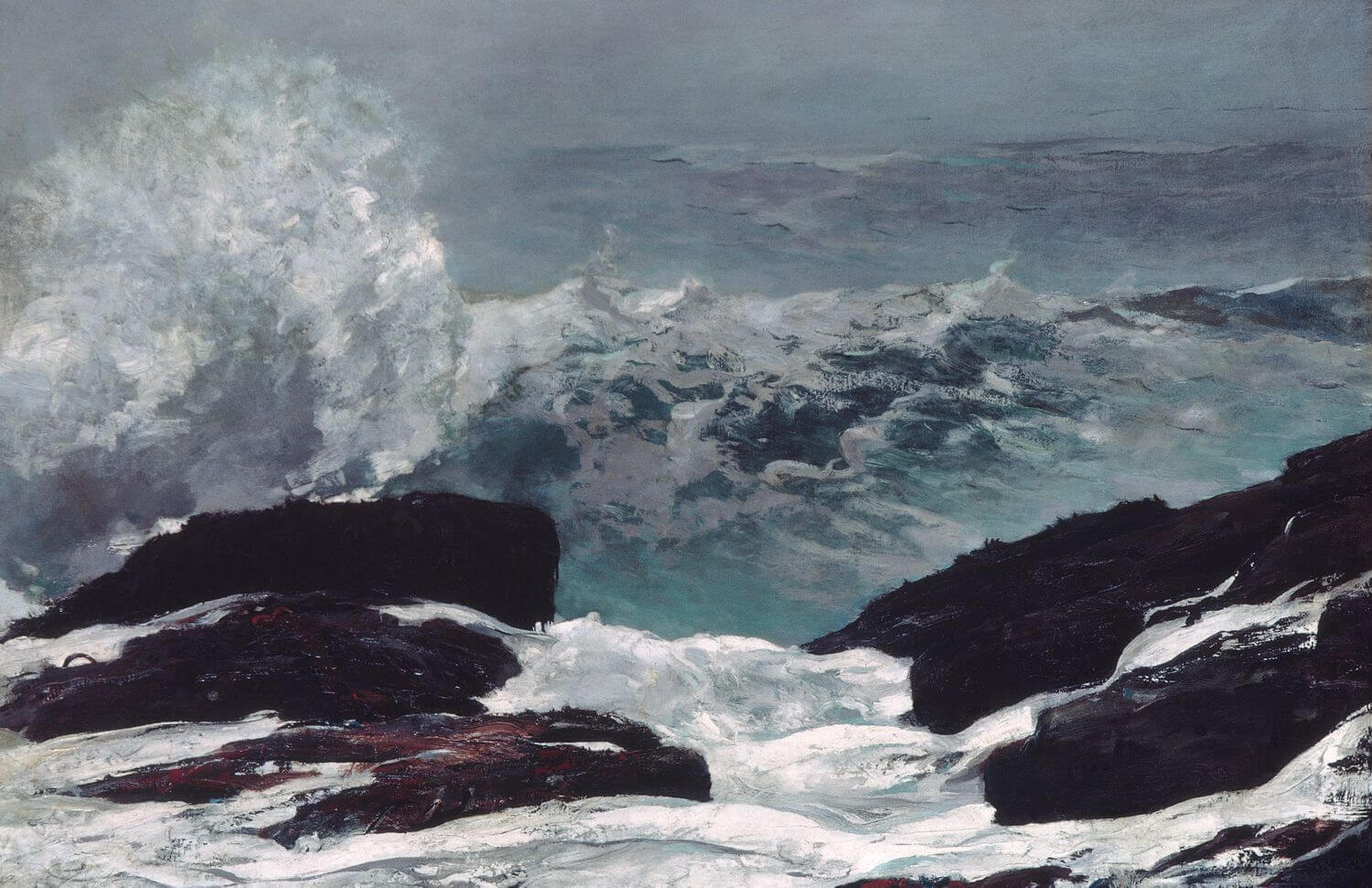type
status
date
slug
summary
tags
category
icon
password
Description
车速升到九十迈以后,他们就再也没能分清重力的方向,几乎以为车身的顿挫预兆着分身碎骨。然而只不过是踩刹车停下来了,这趟失重的旅途没能让他们抵达宇宙中任何一颗星体,甚至也没有离开这片广袤国土,没有逃离这一夜月光照彻的地方。波波夫拽着车门想要爬起来,门一松懈就让他整个身体滚落到地面上,不过事已至此他不再介意满身都沾染了落败腐朽的树叶,因为即便是如此软弱的东西,也让他感到些许可靠:他还活着。身体的记忆缓缓苏醒,狂飙中颠倒错位了好几轮的内脏被牵拉着回归原位,他不再错觉心脏泵出的血液炽烫难耐,一对肾脏为他尚未耗尽的勇气而痉挛,肺部大开大合捕捉着空气,汽车散发的干热气团入侵了这片兀自老去的树林,罪魁祸首无疑就是他身边这位见鬼的老伙计,自己走下车来搀扶他起身的加弗里洛夫。
“阿廖沙,给我来支烟。”加弗里洛夫“啪”地一声把皮手套摔在车座上,好像是用手帕擦干了掌纹里的汗水。
“尼古拉你自己一个人见鬼去吧!”波波夫哽塞着,一出声就哑了嗓子,回到车座上的时候敞开了大衣,仍用拳头抵着心脏,“想抽烟你自便,反正我得再缓缓。”
他们相识的数十年间,加弗里洛夫绝大部分时候都还没有抽烟的习惯。波波夫其实也抽得不凶,不过是因为年轻那时候和工人朋友快速打交道,大家总喜欢坐在河边一起吞云吐雾。在织布男工小伙子缝缝补补的衣兜里,那些纸卷碎屑和烟草末似乎永远也清理不干净,最终全部参与了一次国家政权更迭。如今再随意跟人交换烟卷就不合适了,波波夫更常运用和他这个身份职位相匹配的语言艺术来表达友善,但是随身带烟的习惯还没完全改变,加弗里洛夫只要在波波夫身上一摸就能找到他们当年漏下的革命零花钱。
尽量不要和吸烟的人呆在一起太久;请避免摄入酒精或者含酒精的食物;近期不适合与妻子同房。加弗里洛夫仍记得护士传达给他的嘱托,那时候他刚领到莫斯科医院给的处方,正要去高加索疗养度假,临走前一个年轻的女孩子照着一张纸条逐字逐句念给他听,停顿下来的时候会在口罩后面微笑,念完把纸条折一折,塞进加弗里洛夫左胸前的衣兜里,扣好扣子,另一侧衣兜装着今日这份对抗胃酸过多的药粉,加弗里洛夫料想纸包和字条说不准可以拼成一张完整的纸,但他首先根本不想打开那包药。三则给病人设置的戒律加弗里洛夫已经违反了两条,仍侥幸没有遭受任何惩罚,第三条即便被遵守下来,也不过是因为妻子仍不在他身边。
这一次波波夫的裤兜里面已经没有烟了。加弗里洛夫别无异议,随手放任火柴盒坠入大衣口袋底部。那是他昨夜用来诱惑小娜塔什卡的魔术道具,波波夫自己一个人照顾起两岁的小女儿捉襟见肘,加弗里洛夫哄住孩子能让他好歹打个盹,得省着点划。孩子们一向很容易喜欢加弗里洛夫,因为他让孩子们一起玩弄他刻意蓄留下来的金黄长发,娜塔什卡年纪太小,不懂编辫子,还是看着这个父亲般的金发男人为她玩火更加有趣,大概是因为在火光中,他消瘦的脸看起来没那么苍白了。
波波夫将为他渺小的疏失付出代价。“不在那儿!你摸到我裤裆里去了。”他睁开眼睛却当真看见了伙伴以他素来如此的干练拆解着他的腰带,翻找出因紧张情绪而充血的性器,蹲下来认真抚摸了两下,随后陷没在一片温热的黑暗中。尼古拉不嫌这时候味道积攒得太过浓烈吗?最近几年那家伙的喉咙变浅了,浅得让波波夫害怕在自己的阴茎上看见加弗里洛夫掺入粘液的血丝。
加弗里洛夫回去以后连夜刮掉了胡茬,他分明是故意的。加弗里洛夫脱下厚大衣蒙在头上,波波夫看不见自己胯下正发生着什么,只是感到自己挺翘的性器从顶端开始被濡湿,被一条习惯于发号施令却实在柔软的舌头缓缓绕圈按摩着,连有弧度的棱边也没有忽略。加弗里洛夫嘴里忙活,闷在大衣之下偶尔发出兴奋的呜咽声,像是依恋着品尝顶端渗出的液体味道。如果是在从前,他们一并狂奔甩掉宪警走狗,跑最快的那个要给对方做口活,如今想来真是在错乱的年代做疯狂的事,要是因为太爽忍不住叫出声引来追捕,以后他们谁也别想再和对方性交了。
但那些记忆当然不是他们的最后一次交合。加弗里洛夫再次像从前爱做的恶作剧那样,以吮吸的方式一吞到底,下颌骨撞在伙伴的耻毛上,而后舌尖着力顶起波波夫阴茎下侧那条地带,又将他完完整整吐露出来,只用嘴唇轻吻着他们之间最后一点黏连的液体。那必然是炽天使般极为璀璨的黄金长发从加弗里洛夫耳畔滑落,痴缠在波波夫性器的柱身上,在他被惊扰得绷紧了下腹肌肉之后悄然顺着它原本的线条轻轻抽离。
“……让你赢吧,但我现在还不想交待在你嘴里。”波波夫舒服至极地哀叹道,“把你搞吐了算是让我惹上个大麻烦。”
“那你想射在哪里?嗯?”加弗里洛夫“腾”地从大衣下面冒出他金黄的脑袋,用膝盖登上车座,靠得太近了,凑近波波夫的呼吸里面还带着他下半身那边独特的温存意味。波波夫一瞬间觉得自己咬牙切齿的模样太过颓败,于是猛然迎接了挚友送上来的亲吻。金发编织而成的帐幔笼罩了他们的面孔,那略带腥味的气息中没有血,但他此刻很想亲自咬破加弗里洛夫口中的黏膜。还是太瘦了吗?加弗里洛夫的髂骨被波波夫揽在怀中,割得人手疼。
“……我从医院回来,被他们一起洗了个彻头彻尾。现在里面比外面还要干净。”加弗里洛夫一向有种稚嫩的羞耻心,此刻却轻笑着捉住了挚友的手腕,邀请他来实地感触自己隐秘的腹部。那地方很有可能真的什么都没有,没有什么要遗留给他一生的挚友。
“混蛋,你还是多少长点肉吧。”波波夫隔着衣服捏住了一处相当过分的臀肉。
出路就在那里,波波夫凭手感确认,早些时候就已经被润滑过了,是医生运用在教学模型上没有错漏的手法。但是很少有橡胶教具具备常年骑马的锻炼效果。加弗里洛夫不让波波夫的手掌离开腹部,亲手将挚友的性器对准了穴眼。没入直肠的过程相当顺滑,直至最后就位,在深处戳弄出一点圆满的动静。加弗里洛夫满意得舒了口气,掀开衣襟,波波夫看见那侵染了月色的凹陷腹部也苍白得恍若在发光,肚脐的浅壑如同一道箭头,锋镝直至下腹被阴茎戳起来的小丘。波波夫用手掌感触着那处凸起在加弗里洛夫贫瘠的腹内反复滚动,如同在一盘棋局上拈着君主的廉价替身举棋不定。
“原谅我,亲爱的阿廖沙,这地方我始终只情愿让你一个人这样进来。天底下只有你该知道我又不体面了。”加弗里洛夫跨坐在波波夫身上起起落落,披散的金发之间掩映着一个怆然的微笑。
别这样易于感伤。波波夫想要出言安慰挚友,转念却又噤声。
加夫里洛夫全都知晓。对于检查的程序来说,此事已经和医学没有太大本质关联了,百万兵马的领率者、革命大业与内战的英雄、死战求生的主宰,也无异于那些从废墟中归来的肉块被整合到一起去,被提炼成了纯粹的政治问题。如果他们想要的是一堆听话的死肉,至少在死之前还有很多生命的痕迹要铭刻下来。快感的锋刃在天然为此而生的刀鞘之内厮磨徘徊,这仍不是加弗里洛夫所求的巅峰。
波波夫像是听懂了加弗里洛夫的心声,狠狠拭去了挚友身体中间那道浅显的阴影。加弗里洛夫被命中了,内脏的反应先于神志狂乱起来。那是一道内外夹击的临场战略,磨合至此,波波夫不难从里面用性器触摸到肚脐的高度,拇指在那恰当的时机从外侧将凸起猛然间按回深处,力道贯透了挚友的腹背,迫使加弗里洛夫被合力固定住的身躯痉挛着反向弓身,瘦削的肋骨也伸展开,托举着他向天空伸长的脖颈线条。波波夫维持着侵略的力道迟钝地挪开,短指甲在加弗里洛夫尚且无瑕的腹部勾刮出一道扭曲的红痕。
“……就这样来尽情疼爱我吧,我的朋友。”加弗里洛夫竭力将挚友的头拥入怀中,要他谛听上一次高潮回荡在心中的余韵。波波夫隔着衣服啃咬住一侧胸乳尖端,料想那地方一定被摩擦得红肿不堪。他们有刮痕、吻痕、鲜血、精液、汗水、交合所散发的独特气息和肉体中淫乱的无限潜能在月下淋漓挥洒,形成了一条光亮跳跃的小径,有此为证,必然不同于死。
在尸检报告上用红铅笔作出指示过后,腰杆笔直的人驱车重回到半老的树林侧畔。即便地处郊外,病房中那种令他也窒息的沉闷氛围仍没有消散殆尽。他行至积雪的树林深处,终究冲破了大雪对嗅觉的封杀,追究出一丝异样。一块手帕斜倚着树根的坡度才没有被这场大雪彻底埋葬,他隔着手套捡起那块可怜兮兮的织物,终于舒了口气。那东西闻起来和加弗里洛夫一样胡来。
- Author:fischia il vento
- URL:https://tangly1024.com/article/work/moon-pathway
- Copyright:All articles in this blog, except for special statements, adopt BY-NC-SA agreement. Please indicate the sour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