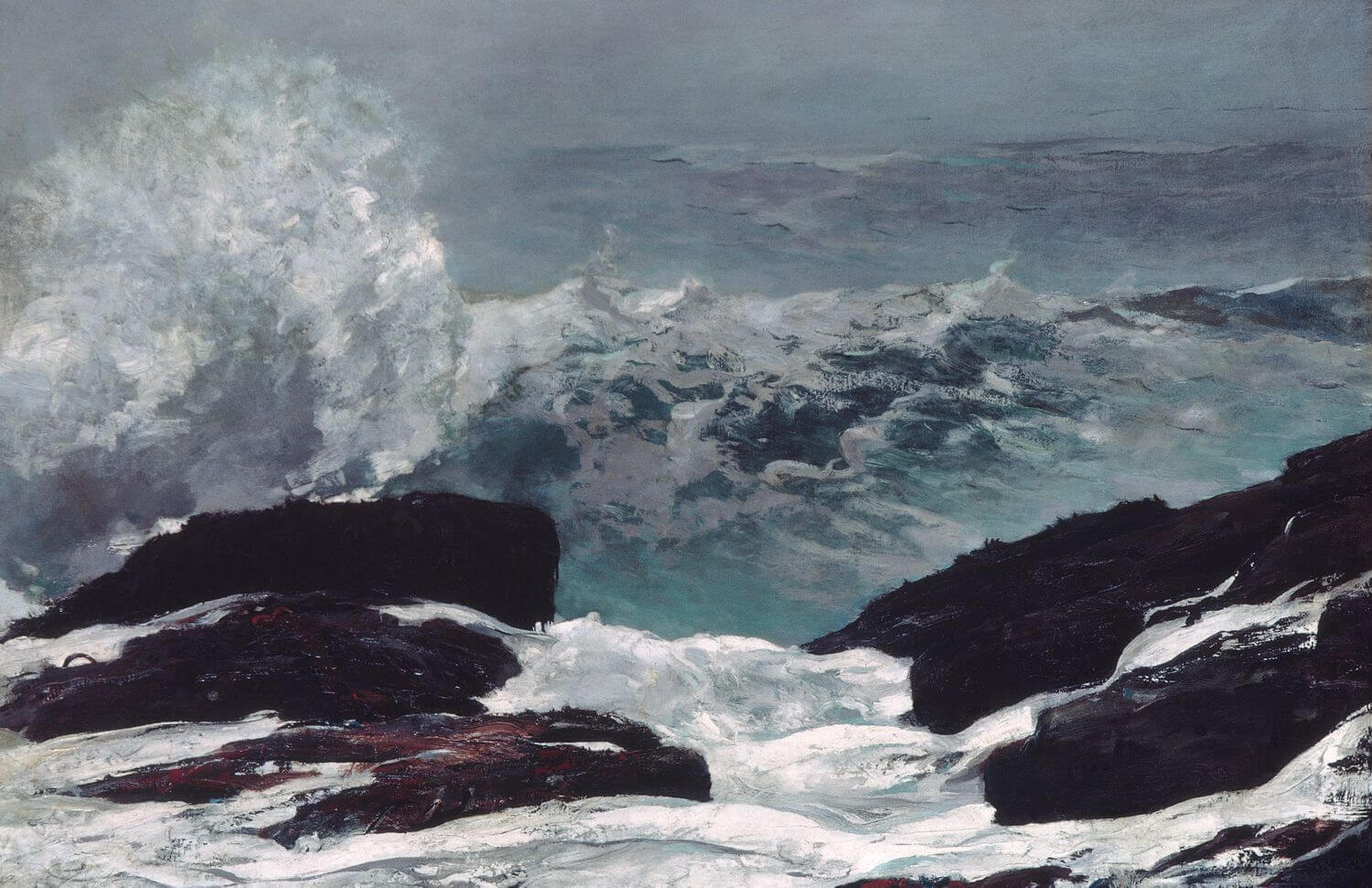type
Page
status
Published
date
slug
translate/ofrunze-k-v-frunze
summary
001-康斯坦丁·瓦西里耶维奇·伏龙芝
tags
category
翻译
icon
password
Description
康斯坦丁·瓦西里耶维奇·伏龙芝(1881-1940)——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伏龙芝的兄长。父亲早逝之后尽心教养弟妹;曾参与日俄战争。毕业于喀山大学医学院,后成为医生;内战时期和战后担任军医。1928年起从事法医工作,1933年起担任塔吉克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卫生委员部国家级法医学专家和顾问,后担任塔吉克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首席法医专家。
米哈伊尔比我年幼整整四岁。他生于1885年1月21日[1],在他之后又有三个妹妹出生。我们的父亲是家乡皮什佩克城(Пишпек,今伏龙芝市[2])一名医护人员,家产微薄,母亲又没有闲暇时间,所以要由年长的孩子来照料年幼弟妹。
米沙很早就学会了走路。他三岁的时候就能流利讲话,总是因为聪明伶俐而显得与众不同。也正因如此,就算我努力逃避照料弟妹的责任跑去找邻居家的孩子,我也鲜少成功甩掉米沙。
离我们家不远的地方是一片苦艾、牛蒡、甘草丛生的荒地,当中有许多毒蛇和毒蜘蛛,尤其是避日蛛。这片荒地就是我们童年世界的止境。为了躲开米沙,我经常躲在草丛中,或者和同伴一起挖掘美味的甘草根……
后来,这片荒地也成了米沙躲避家里麻烦事的避难所,由于他顽皮好动、喜欢搞恶作剧,他时常需要逃出去。
我弟弟直到生命的最后几天都对狩猎充满热情,这是从我们父亲那里承袭来的。当年,皮什佩克周围到处都是猎物,既有飞禽也有走兽。冬天,我们的父亲经常在家里的花园中射杀野鸡,镇上每家每户都至少有一支猎枪。春秋两季,我们就准备弹药,装卸枪支。米沙和我也乐于参与,不忘倾倒火药,用自制枪射击。由于我较为年长,父亲去打猎时会带上我,叫我帮忙看护马匹、生火、烧水。对我们这些孩童来说,摆脱污浊的城市尘嚣到旷野与山中,能享受到非常快乐的时光。
米沙则被留在家里。他天性活跃,热爱冒险,很难保证他不会跑到掠食性动物出没的芦苇丛深处。试想在狩猎这种非同一般的活动中要怎么甩掉米沙!他经常钻进马车前端,蜷缩起来用什么东西盖住自己,以免被发现。如果不使出拼命的力气就没法叫他从那里出来。
米沙跟上父亲和我去打猎的另一种方式是和我提前串通。通常我会在出发前知道父亲要去哪里,所以可以透露给米沙。当父亲和我出城一里之后,父亲就会惊讶地发现一个小猎人赤着脚,穿着衬衫和背带裤,一手持鱼竿,另一只手捏着面包,正勇敢地走在旷野上。没有办法,这样我们就只好带上米沙一起走了。
有些时候,米沙也会被领回家。他只能在类似狩猎的游戏和活动中寻求安慰,有一次招致相当严重的后果。有次出去狩猎,我和父亲在城外几里看到城内升起一股烟柱,就在我们家上空。我们赶回去,发现房子的谷仓和干草垛都烧毁了。
直到深夜米沙都不见踪影。听到母亲和妹妹们在哭,父亲大喊着保证不惩罚他,躲在院子里白杨树顶上的米沙才高声应答。原来他为了在同龄伙伴面前表演打猎的场景,在谷仓和草垛之间点了一把火。
此事之后,米沙就在马车后座有了一个不可剥夺的席位,甚至可以坐在车夫的位置上,一手牵着车夫(通常是父亲或者我),一手执缰绳或马鞭尝试驾驭马车。
米沙也承袭了父亲爱马的情怀。当时我们父亲管理的地方诊所就位于我们家庭院的附属小楼中,每天都有原住于塞米雷奇耶(Семиречья)的吉尔吉斯游牧民来就诊,病人都很乐意让跃跃欲试的米沙骑上马。
我们父亲的诊所没有其他工作人员,实在需要用人就只能求助于我们这些孩子。我们要捣药、包药粉、在一些简单的手术中当助手。拔牙是父亲最为娴熟的技艺,总能使病人满怀钦佩。我之所以提到这点,是因为米沙七岁时就帮父亲完成了一例成功的手术,几天后病人带着一匹小马驹登门致谢。米沙很快就驯服了这匹小马,以至于小马当即就对米沙给的昵称有所回应。
米沙很早就能读书了,当时他大约五岁。我在弟弟面前写作业也促进了他识字,他天生充满好奇心,喜欢较真,不可能不向他解释词语的含义和上下文联系。
到了七岁的时候,米沙已经能读祖母教给我们的教会斯拉夫语了。同年,米沙熟练掌握了拉丁字母。我不记得家里或者周围熟人中有哪些专门供儿童阅读的书籍。我们的父亲有几本看标题就很难懂的医科书籍,除此之外,我能想起来的就是C. M. 索洛维约夫(Соловьева)写的两卷本《自远古以来的俄国史(Истории России 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3]。米沙和我认真研读了这两本书。我们还阅读《光明(Свет)》周报的增刊,其内容通常是翻译过的法国小说。
这里没有什么公共的表演或者娱乐活动,对大人和孩子来说都如此,只是偶尔有一些从乌兹别克或印度来的人路过这里的时候会变魔术、走钢丝。除了这些客人之外,塞米雷琴斯克地区军事长官或者驻韦尔尼(今阿拉木图)的突厥斯坦主教来访也会牵动城里的公众生活。
某次主教来访引发了一件趣事,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来米沙自尊心的早年发展,以及他毫不容恕暴力的态度。主教仪式通常由男生参与,负责托举燃烧蜡烛的烛台和各种教堂礼仪器物。我们学校的老师也让米沙参与这项工作。礼拜天前夜,祖母从夜祷仪式接弟弟回来,并告诉我“米沙受到了极大的礼遇”,他穿礼袍、持圣器走在主教前面。
米沙和我睡一张床。那天夜里他辗转反侧,最后终于将心里的疑虑说了出来。原来大主教区仪式上有一位助祭长,凭靠身高和声音颇为引人注意,为了维持秩序会敲打这些小小年纪的参与者,米沙受冤被抽了两下。我安慰他,说他现在已经熟悉了礼拜仪式,明天弥撒的时候就能轻松些了。
清晨,祖母很早就来接米沙去教堂。后来我们全家都去了,我们看到米沙和司祭的儿子一起,身穿节日衬衫,外罩锦缎礼袍,手捧长烛台,站在圣门两侧。
看到我们的主人公庄严地走在主角前面,我们家人和邻居都很欣慰,但这圆满的一幕并没有持续下去。主教仪仗队井然的秩序突然被人以最骇人的方式打破了:米沙突然转向身后的助祭长,把烛台硬塞给他,然后在众目睽睽之下将自己闪光的衣袍扔在助祭长头上,丢下一句“谁叫他揍人的,衣服留着他自己穿吧”随后就挤进了这群目瞪口呆的虔诚教民中。
过了一阵,我在荒地隐秘的灌木丛中找到了米沙。我弟弟没有一丝自责的念头,唯独后悔宣告自己脱离“天使的行列” 太过武断又太溢于言表了,惹得祖母不高兴。
七岁的时候米沙开始上学。当时,城镇里唯一的堂区学校被改造成了市立学校,课程内容拓宽,学制从三年延长至六年。高年级开始学习几何、代数、自然科学。
市立学校开学,有两位新老师从圣彼得堡来此就职,小镇陈腐的生活焕然一新。除了走亲访友和各种家庭庆典,如洗礼、生日派对,或者硬着头皮消耗酒和馅饼,城镇居民有了前所未有的新兴趣。我们这些孩子听到了类似于“戏剧”“合唱团”的新词汇。
К. Ф.斯维里切夫斯基(Свирчевский)老师指导年轻人每周聚集在我们家演唱世俗歌曲。他还指导了皮什佩克的第一场戏剧,上演Н. В.果戈理的喜剧《婚事(Женитьба)》,我们全家都参与了。米沙和我听着家里排练演出的声音,将剧本背诵得谙熟于心。
也是那年秋天,我去了韦尔尼上文理中学,从此和进入市立学校二年级的米沙分别了将近两年。我回家后有两样东西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文理中学制式的帽子,还有我因为取得进步、表现良好而赢来的米哈伊洛夫《阿尔汉格尔斯克省森林狩猎》[4]一书。两样东西都归了米沙所有。
在那时,我们家度日艰难:父亲失去了在皮什佩克的差事,走投无路只能去邻近的锡尔河省当医护人员,两年后在那里去世。我们全家搬去了韦尔尼,米沙也进入了我所在的文理中学。
父亲去世前卖掉了我们在皮什佩克的房子,我估计卖了四百卢布。我们从中得到了一部分财产赖以维生,直到秋天的时候,皮什佩克城镇政府感念父亲长久以来的效劳,同时也为了奖励米沙在文理中学出色的成绩,向我们家发放每月十卢布津贴,一直到米沙毕业为止。除此之外,我给不及格的低年级学生补课也为家里挣到了钱。
这些学生要么是米沙的同级生,要么比他年纪更小,所以我备课的时候米沙帮了大忙。有时候,我给学生讲题目或者句法规则无论如何都没把对方讲明白,米沙却能用自己一套古怪的方法把理解力最贫弱的学生教会了,日后他也因此被称赞为技法娴熟、经验丰富的小老师。进入文理中学高年级之后他不再寻求补课学生,但是也一直有学生主动找到他,竞相邀请他来当家教。他自己则以优异的成绩取得了金牌[5],从文理中学光荣毕业。
我就读于文理中学的最后两年,我们家搬回老家皮什佩克居住,因为母亲在老家还有些亲戚,那边谋生活也比在韦尔尼更容易些,我和米沙跟家人分开了,两年来都寄住在官僚家庭,给官僚子弟当家庭教师换取食宿。
我弟弟永远都仪表洁净,总是把我传下的旧衣服洗得干干净净,褪色了就重染,破损了就缝补好。他每个月都去理发店剪一两次头发。总的来说,他令人赏心悦目:工正而不呆板,整饬而不矫饰。
我从文理中学毕业前一年的暑假,我和米沙回家看望母亲。我们搭乘乌兹别克人的马车沿着通邮路线走了五天,中途在一个荒无人烟的驿站停下,在吉尔吉斯人墓地上名叫“穆卢什卡(муллушку)”的四方形圆顶土造建筑里面过夜。
我们兄弟两个都忽略了毒蛇和毒蜘蛛喜欢栖居在这种地方。清晨我醒来,看向躺在身边的米沙,惊恐地发现有一只巨大的避日蛛在他赤裸的手臂上。我吓得不敢轻举妄动,害怕触怒避日蛛,干等着它爬走,或者爬到我弟弟身上有衣服覆盖的地方。
我的目光落到米沙脸上,发现他睁着眼睛,和我一样仔细观察着避日蛛的动向。许久,避日蛛终于从米沙手上爬到地上,这才被我用帽子拍死。惊魂既定,我问米沙什么时候睡醒的。他说避日蛛一爬上来的时候自己就被刺醒了,知道这种虫子非常易怒,所以纹丝未动。
米沙在这种特殊场合表现出强大的意志与忍耐力,除此之外他还有一种出众的品质,那就是会以世人罕有的毅力坚持实现目标。他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学会了我们中学生之间时兴的国际象棋。下棋对我们来说不过是娱乐消遣,但是米沙却当即把它看成一门学问来研究,半年后就击败了中学生里的佼佼者,有一次还代表我们中学赢了与塔什干一所文理中学的联赛。
1900年,我中学毕业,进入喀山大学医学院,当时米沙上五年级。整个大学阶段我都没有机会回家,但这无法阻止我与家人保持联系,尤其是和米沙。九十年代初学生运动的讯息通过报纸、我们亲属之间的密切通信以及其他途径传播到了塞米雷奇耶。许多学生、革命知识分子、工人被逐出首都和大学所在地来到这里,向年轻人介绍革命活动和文学作品。当初我们留给后辈学生的文理中学自学小组致力于研读历史、哲学、自然科学文献,拓展学校教学内容,弟弟在寄来的信表明这些自学小组已然大改,主攻政治经济学为主的社会科学,开始具备革命色彩和斗争性,第一步就是要求校方停止学生宿舍突击检查、不得强迫学生参加宗教仪式、停止欺凌贫困学生等等。
声明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于是实际行动接踵而至:一个以无孔不入著称的督学被一群蒙面人堵进僻静的花园里殴打。米沙写道,自此以后,学校里就弥漫起武装中立氛围。
1904年,米沙中学毕业,升入圣彼得堡理工学院经济学系。起初他领我空出名额来的那份塞米雷琴斯克地方政府助学金,不久之后他就在圣彼得堡找了份差事,全身心投入革命工作。
1905年11月,我从日俄战争中归来才与米沙短暂见上一面。[6]
1906年夏天,我在喀山省奇斯托波尔(Чистополь)区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基(Петропавловск)村担任地方自治局医生,米沙出其不意来找我共度了一个月。当时情状焦灼,奇斯托波尔的地主积蓄与田产正在瓦解,俄国其他地方也一样。我弟弟为了不连累我而用了假名字来我身边。他看起来疲惫不堪,有胃黏膜炎症状,但很快就康复了。
初秋,我不在的时候米沙收到一封加密电报,要求他立刻离开。要穿过六十里艰涩难行的泥泞才能到城镇,我骑马赶回来时马已经累得几乎站不住脚,但是没有什么可以牵绊住米沙,找不到另一匹快马就把这匹乏力的马喂饱。我们星夜兼程赶往奇斯托波尔市,换乘最早一班货运客船前往喀山首府,然后米沙独自坐上前往莫斯科的列车。
我弟弟被拘禁在沙俄监狱里那数年间,我只有1908年初在弗拉基米尔侦查监狱见过他一次,为此需要花上几个月的时间来准备。也正因此,我才见到我弟弟在弗拉基米尔、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舒亚那些幸存下来的同志,并领略阿森尼在这些城市的工人阶级群体当中有着巨大威望。
我和米沙会见了十分钟,隔着两道铁栏杆,有两名狱警在场监视。我在米沙身上没有捕捉到一丝绝望或者他对自己命运的担忧:他用最开朗愉悦的语气谈论在监狱里组织木工作坊、他自己学习语言和哲学的事。
《М. В.伏龙芝:朋友与伙伴的回忆》。莫斯科,1965年,第11-20页。
М. В. Фрунзе.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друзей и соратников. М., 1965, с. 11—20.
[1] 公历 1885 年 2 月 2 日。—— 译者注
[2] 原文如此。皮什佩克 1926 年改称伏龙芝,1991 年苏联解体后改称比什凯克,今吉尔吉斯共和国首都。皮什佩克(Пишпек)与比什凯克(Бишкек)读音相近, 拼写上有区别。—— 译者注
[3] 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索洛维约夫(Сергей Михайлович Соловьёв)《自远古以来的俄国史(Истории России 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圣彼得堡公惠出版公司(Товарищество «Общественная польза»)1851-1879 年间出版,全书共 29 卷。——译者注
[4] 亚历山大·康斯坦丁诺维奇·舍勒(Александр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Шеллер),常用笔名A. 米哈伊洛夫(A. Михайлов)《, 俄罗斯白海地区的自然和生活速写:阿尔汉格尔斯克省森林狩猎(Очерки природы и быта Беломорского края России : охота в лесах Архангельской губернии)》。——译者注
[5]正式名称“优异学习成绩”奖牌(медаль «За особые успехи в учении»), 时为俄罗斯帝国奖励中等通识教育优秀毕业生的制度,帝国绝大部分高等院校都可以免试录取获得该金质奖牌的学生。——译者注
[6] 1904-1905 年日本与俄国争夺中国东北和朝鲜地区霸权的帝国主义战争,由日本发动,以 1905 年签订《朴茨茅斯和约》结束,催化了俄国 1905-1907 年革命的爆发。——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