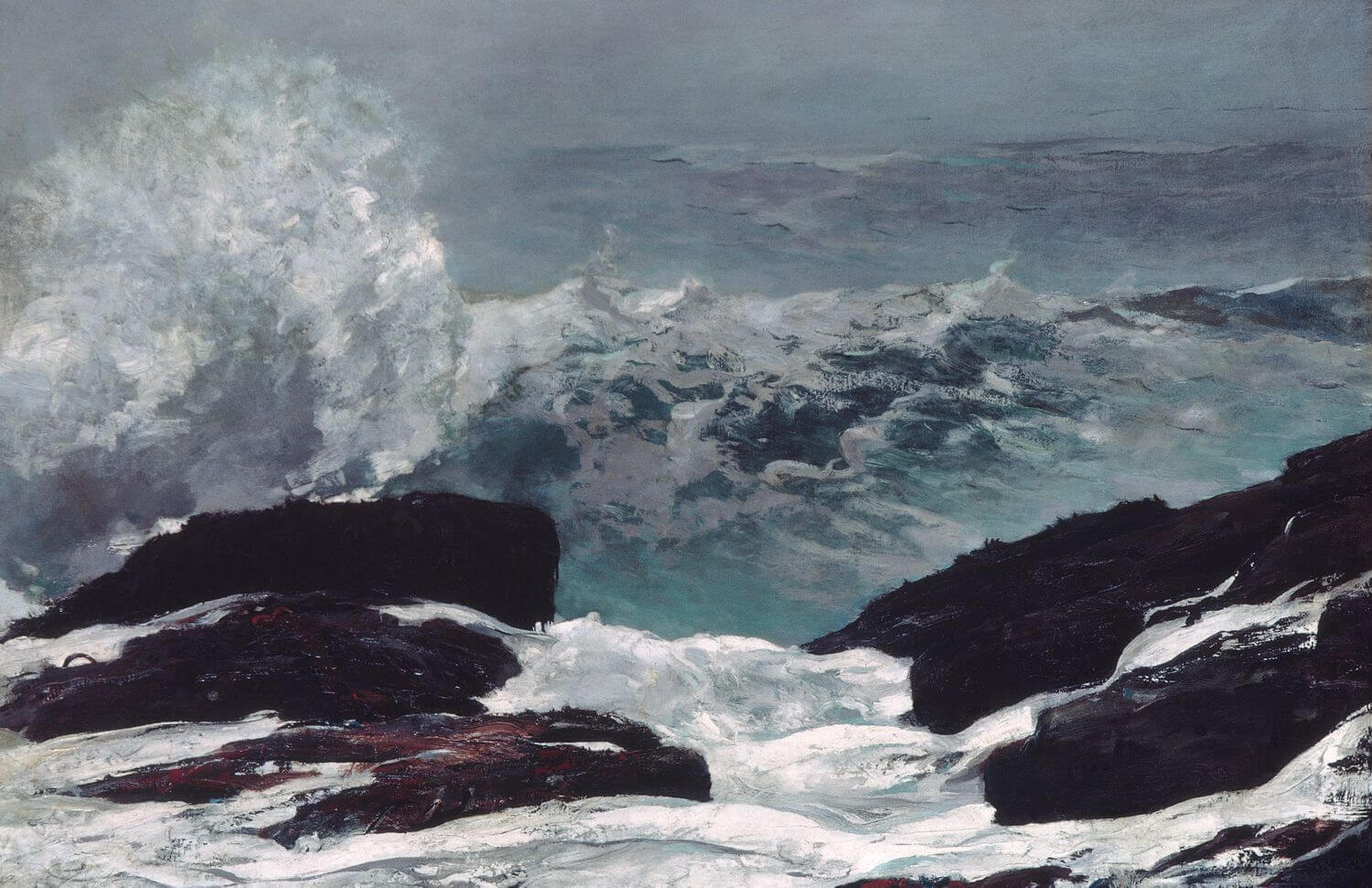type
Page
status
Published
date
Nov 10, 2025
slug
manage/moon
summary
关于皮利尼亚克《不灭的月亮的故事》的思维发散,恶政隐背后的纯爱却令人暖心。
tags
不灭的月亮的故事
category
考据整理
icon
password
Description
1926年1月,皮利尼亚克小说《不灭的月亮的故事》发表于苏联文学期刊《新世界》,故事的主人公加弗里洛夫是一名红军高级指挥官,被当局一个“不折腰的人”强迫做了本没有必要的手术,最终死在手术台上。文章一经问世就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尽管作者在卷头语中否认道:
本篇情节可能使人产生这样一种想法,即作者的写作动因和素材都源于米·瓦·伏龙芝之死。其实,我与伏龙芝并无私交,只是见过一两次,认识他而已。我不了解伏龙芝死亡的真实细节,而且这些细节对我也无关紧要,因为我这篇小说的目的原本不在于报道这位军事人民委员之死。我认为有必要向读者说明上述情况,免得读者在这部作品中寻找真人真事。
当时距离伏龙芝意外去世还不到两个月,人们的哀悼和怀疑情绪都难以消停,所有能看到这篇文章的人都只会觉得,这份免责声明不过是苏制“此地无银三百两”。既然加弗里洛夫取材自伏龙芝,那强迫同事的机械主义头领“不折腰的人”是不是就对应着斯大林呢?——作者写这篇文章是想要指控斯大林用政治阴谋害死了伏龙芝吗?
皮利尼亚克很快就遭受了严厉指责。这篇小说被抨击为“反革命,对中央委员会和党的诽谤”,作者本人和杂志编辑部被迫公开认错,献题对象沃龙斯基被迫表态割席,批准本作出版的审查人员也遭受降职处分。所有已经发行的杂志都被没收销毁,就此成为苏联禁书。皮利尼亚克随后的命运似乎也照应了他在本作中所反思的政治阴谋,1937年,他在斯大林发起的大清洗中遭到枪决,成为和笔下角色一样的牺牲者。沉寂了半个多世纪以后,“不灭的月亮”那疯狂而冷峻的光辉才重现于世。
从一开始,这篇文章就不能当成独立的文学作品来解读,必须要结合历史上的政治时事。
我注意到了中译的皮利尼亚克小说集或者苏联禁书文学汇编在前言后记当中向读者补充了相关的历史信息,然而叙事上有些疏漏,可能会在百年之后继续造成误解。下文我将尝试给出不一样的看法。
译本选取
Anna’s Archive上容易获取的电子书版本如下:
钱诚、张敬铭译《不落的明月》
刘引梅译《皮利尼亚克小说选》
石枕川、王少孔译《不灭的月亮的故事:皮利尼亚克小说》
顾永忠译《不灭的月亮的故事》
石枕川和顾永忠译本当中删节掉了一些尚有解读价值的文段,因此不推荐用这两个版本来初步了解本文。刘引梅译本pdf油墨太浅了看着有些费眼力,且前言后记中的补充信息不如钱诚译本丰富。下文将以钱诚首译本《不落的明月》为主要参考。
文本解析
我在文学和语言学方面主要求助于赛博列宁站上的这两篇论文/教学方案,现总结如下:
Вы точно человек?
«Цека играет человеком…» («Повесть непогашенной луны» Б. Пильняка: поэтика экспрессионизма)
Исследователь обращается к повести Б. Пильняка «Повесть непогашенной луны», наиболее репрезентативной для понимания творческой индивидуальности художника учащимися. Анализируя систему персонажей, сюжет, систему мотивов, тему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 и поэтику в целом, автор выстраивает и логику усвоения непростого текста школьниками.
皮利尼亚克注重用文字构建富有画面感的空间结构,故事坐落于一座阴霾密布的城市当中,心理氛围极端压抑,已经到了和市民生活格格不入的地步。接下来,列车载着异域的自然生命气息驶入,打破了死气沉沉的城市图景。波波夫扮演着读者的向导,前来迎接主人公加弗里洛夫登场。在正式见到主人公之前,向导角色还遇到了一些触发人机对话的NPC守卫士兵,他们就像是城市机器这个宏大景观的一部分。人性——非人性二元对立已经反复出现,接下来最集中体现这种矛盾冲突的就是主人公加弗里洛夫。
作者介绍加弗里洛夫人物设定的方式近乎堆砌和灌输,如果出现在一篇普通文学当中则有生硬之嫌,但是考虑到本文强烈影射着现实人物,这些描述在本文之外有确切的支撑,因此在这里不计较文字的说服力问题。读者看到的加弗里洛夫是一个富有反差性的角色:他在社会身份上是军事统帅,“拥有足够的权利和意志力,能够指派人们去杀死他们的同类并自己奔向死亡”,作为整个国家机器想要良好运转所必须的一部分,他的这重属性是非人性化的。但是在个人层面,他身上又具备非常强烈的人性潜质。军服不合身,靴子磨损,神情温和疲倦……这些肖像画上的细节都削弱了统帅形象带给人的冷酷感受。他在战争年代的传奇经历则富有炽烈的浪漫色彩,充满生命活力,也与城市机器的死板迥然不同。波波夫被设定为加弗里洛夫的竹马好友,两个人之间有很多共同回忆,有了这层关系铺垫,作者描写了两个熟人老朋友的对话,读者也得以在叙述和描写的交织中一窥他们曾经的生活经历。这部分内容也致力于表现人性、生活,即便他们已经成为高级政治人物,依然在彼此面前保持着亲昵。
从加弗里洛夫出场开始,他的自我意识一直压制着社会身份,在参谋和列车员面前表现从容。随后,波波夫开始与他谈论此次被召集到这座城市可能要执行的任务,加弗里洛夫内心的平静被打破,变得焦躁不安,主宰死亡的至高统帅开始恐惧死亡,甚至恐惧着这个会表现出懦弱属性的自我。后文当中,加弗里洛夫因患病而被诊断为伴有轻度神经衰弱,这种心理上的紧张可以延伸到前文,人性与非人性之间的矛盾不仅被读者看见,也不断拷问着主人公的内心,所以加弗里洛夫才会在言谈中将自己分裂成了两个人:代表生命力和个人属性的织布工小伙子,代表机械、社会属性的统帅。疾病则对这两重人格漠不关心,只管将两个人格凝聚在一具肉身上。
为了消除对调令的疑虑,加弗里洛夫去见了“不折腰的人”,再一次戴上了统帅的面具,语言风格不再像前文那样优柔,而是变得严厉果决,试图掩盖内心的恐惧和犹豫。但是“不折腰的人”在社会身份上比他地位更高,非人性化的特质更强烈,因此加弗里洛夫在这场他鼓起勇气努力面对的谈话中落于下风。在“不折腰的人”眼中,加弗里洛夫患病不是个人不幸,而是庞大的国家机器中一个小零件出了故障,他关心加弗里洛夫的方式不是像波波夫那样对兄弟表现出同情和关切,而是下命令让病人尽快做手术修复问题。如果不考虑后文中病人死亡的结果,“不折腰的人”这种非人性化的、机械主义行为其实说不上有什么个人阴谋和恶意。
皮利尼亚克如何表现“不折腰的人”这种非人性化特征?加弗里洛夫带着直白的外貌描写登场,写到“不折腰的人”出现时却“看不清他的脸”,直到这个场面结束很久之后,作者的摄影镜头才对准了他的面容、肢体行为,可即便如此也没有再交代出任何人物信息,读者不会像面对加弗里洛夫和波波夫一样感到可亲,感受不到此人的灵魂与激情,换言之已经是一台绝对的政治机器了。
“不折腰的人”下命令调遣来的医疗团队被塑造成了整个厄运故事的附庸,也是失能的见证者。加弗里洛夫纵然是主宰死生的统帅,也因人类肉身的脆弱性被贬低了,在医生面前用询问要不要脱去外衣,用军事统帅下命令的语气求一个被使唤被摆弄的卑微结果。对抗和怀疑不折腰老大哥的意志已经让他感受到痛苦,这种行为就体现了主人公正在放弃思考、向机械主义妥协。会诊在严密的氛围中潦草执行,世界果不其然是一个巨大的草台班子。写到此处,皮利尼亚克就已经打破了一般叙事的秩序,提前交代出了这个悲剧故事的一部分结果,即前文中犹豫的加弗里洛夫最终做了手术,而且从作者所设定的事实上来说还毫无意义。
“不折腰的人”继续运转着国家机器,与此同时,加弗里洛夫再一次来到波波夫身边,这场戏的空间环境依然致力于表现非人性,但是人物之间发生的事情却努力维持住了人性温暖的氛围。加弗里洛夫因为他的社会身份而被迫和自己的妻子孩子离散,波波夫则是和女儿一起被妻子抛弃,三个人组成临时的小家庭。加弗里洛夫给娜塔什卡唱摇篮曲十分生涩,甚至可以说是反常且笨拙了,表明他此前非常缺乏家庭生活体验,现在又迫切渴望,他的人性还没来得及充分表达。两位老朋友在孩子安睡的时候交谈家长里短,最终才将话题引向手术。加弗里洛夫从本心上并不信任被指派来的医生团队,但是又觉得做手术这个命令无法违背。
与波波夫道别之后,加弗里洛夫回到了车厢,通过一系列最平凡不过的动作描写准备休息。由于这个场景中没有对等的角色能与他交流,加弗里洛夫全部都心理活动都诉诸环境、肢体动作和“他人的语言”。车厢内所有关于异域生命气息的描写都消失不见,转而被一种和城市机器相近的死寂所取代。前文已经反复提及加弗里洛夫执着于托尔斯泰的著作《童年与少年》,对他来说,这本书里有“美好爱情、淳朴关系、朴实生活”,有“阳光、人、人间纯真的喜悦”,这都是加弗里洛夫作为统帅感到自己所缺失的东西,并且他没有办法用自己的语言来表达这种缺失,只能求助于他人的语言。一开始他只是认为书写得很好,可是命运降临的前夜,失语的加弗里洛夫得到了开悟的机缘,终于被托尔斯泰的作品激发出了表达自己人生意义的能力,写信的层次重演了他阅读理解的层次。通过后文,我们得知了加弗里洛夫信中所写的内容。他正是在与波波夫父女组成的临时小家庭里下定决心承担牺牲者的责任,将自己势不可挡的死亡转换成一种机会,生命的本质如此脆弱,既然他终究没有办法活成一个完整的人,那就竭尽所能让身边的人有机会被弥补。
有些中译本删节了加夫里洛夫写遗书之后抽烟的动作、邀请波波夫飙车的文段,这种删节行为严重削弱了原作的情感层次。
没有人知道加弗里洛夫一反常态再次吸烟的时候在想些什么,但是下文中再次发生了转折,进入了一次心理情节上的高潮。加弗里洛夫又一次戴上统帅的面具,用强势果断的语气把好兄弟半夜摇醒陪自己出来飙车。此处表现了加弗里洛夫性格中嚣张奔放的一面,在速度中体验逃离城市氛围的自由,将余生活得淋漓尽致、充满激情,抛却了曾经定义他人生的恐惧、软弱、疾病和禁忌。在这段描写中,皮利尼亚克再次采用了按下不表的叙述技巧,像前文描写不折腰之人面貌时那样,汽车被描绘成了一个独立的机械装置,所有极限行为都不受人类意志的控制,直到结尾才露出坐在方向盘后面的加弗里洛夫。通过与机械融为一体,加弗里洛夫在饱受怀疑和虚弱性折磨之后终于可以重整自我内部的秩序,他人性软弱的那部分或许会渴望死于机械失误造成的车祸,但他执行社会功能的机械性的部分则不允许这种失误。加弗里洛夫抽烟的线索至此已经出现三次:第一次抽烟(在不折腰的人的办公室当面戳烟头)——第二次抽烟(在车厢写完遗嘱之后)——第三次抽烟(带着波波夫疯狂飙车之后)。这个行为象征了他的沉思,也带来了生命的温暖,或许也代表了叛逆或者反抗的精神。
第三章开头直接预告了加弗里洛夫会死的结果,实际上整个作品都是用结果倒推出来的,在此重申,独立原创作品这么写肯定要吐槽败笔,但是影射现实的文学就是另一回事了。医生在准备工作中的语言描写足以概括全文:“不是和具体的病人打交道,而是在按照现成的公式办事。”前文当中所有的情感因素都已经铺垫至完满,主人公也最终陷入了丧失主动性的处境当中,不再变化,所以这部分内容主要是交付最终成果,成全一个悲剧故事。作者的人文意图也集中体现在这里,作为病人的加弗里洛夫在医疗过程中被人像处置物品一样对待,甚至连草台班子手术中被命令的附庸都算不上。神魂迷乱的临死之际,加弗里洛夫再次体验到了二元身份交织在一起。接下来,作者在本文中所设定的事实最终揭晓:手术是完全没有必要的,抢救也是完全没有必要的,最终主人公完全没有必要地死掉了,这一切错误都是看似不会犯错的机械主义所指使的。不折腰的人就连哀悼死者都像是照章办事,我们依然无法参透机械人格底下的任何私人情感因素,最终讲故事引向一场没有哀思的葬礼,只有波波夫和娜塔什卡在他们曾经的家里为加弗里洛夫服丧。
历史背景
我写这篇整理帖的初衷其实是应对钱诚译本前言中的这段话:
在这里,我们看到,在某种力量的作用下,人会自觉地放弃自己最基本的权利,会作出违背自己良知的事,有时甚至会把自身生命的支配权交到一个自造的“神”手里,任其摆布,殊不知这位“神”也是个有着七情六欲的血肉之躯的凡人。在旁观者看来十分可悲的事,在当事者思想上或许还正因为自己能够“视死如归”而心安理得,毫不以为苦呢。如果不作“如是观”,我们就很难理解伏龙芝这个热爱生活的人,这位多年驰骋疆场、名震遐迩、使敌人闻风丧胆的军事将领怎么竟会违背自己的意愿而乖乖地躺到手术台上去。想到这里,我们便可以进一步理解小说之所以在1926年引起那场风波了。
译者似乎认为,伏龙芝本人就像加弗里洛夫那样屈服于机械主义,才招致了死亡的结果。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我们先来整理一下译者所认为的“事实”的来源。
译者前言如是补充了皮利尼亚克创作《不灭月》的历史背景:皮利尼亚克经由图哈切夫斯基介绍和伏龙芝相识,之后从图哈切夫斯基的转述中了解有关伏龙芝死亡的信息,因此大受震撼,于是用了三十天时间写完了这篇小说,卷头语也是根据图哈切夫斯基的建议添加上去的,献题对象是沃龙斯基。
译后附注补充了伏龙芝之死的历史背景,主要援引根德林自传体纪实小说《受害的一代》当中的说法,这段引文认为,伏龙芝是因为遭受斯大林的忌恨而被杀害的,斯大林想要动用政治暴力强迫伏龙芝,伏龙芝虽然在个人情绪上不满,但对当局的命令表示服从。
三个证人——图哈切夫斯基、沃龙斯基、根德林,他们的见证足够可靠吗?
- 根德林:
我暂且认为,根德林的话一个字也不要相信。因为《受害的一代》写作出版的时候已经是1970年代根德林移居到以色列以后的事情了,1925年根德林才两岁,他的父辈或许会了解当时的政治细节,但是这段小说文字依然距离伏龙芝案过于遥远,写作口吻像是趴在斯大林和伏龙芝对话现场的桌子底下做史官,也终究也不是真正的近距离纪实,不足以成为可靠的历史依据。《不灭月》译者想要构建历史叙事的时候只采取了根德林的小说,那在结果上也是不可信的。
- 沃龙斯基:
要考察沃龙斯基与伏龙芝的关系,目前我只能参考到加姆布尔格写的回忆文章,此人是伏龙芝的亲信好友兼传记作者,可以获取丰富的一手资料。加姆布尔格的回忆文章补充了传记没写的私人生活内容,现将其中提及沃龙斯基的部分补充如下:伏龙芝担任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省执行委员会主席的时候,经常在工作之余挤出时间阅读文献,当地官方机关报《工人边区》的编辑即是沃龙斯基,经常帮助伏龙芝选取新书,标注其中有趣的内容。沃龙斯基
- 图哈切夫斯基:
人们描述苏联初期政治派系斗争的时候表达出了太多无凭无据的观点,比如中文互联网有人把伏龙芝归类为斯大林察里津派的附庸,把图哈切夫斯基归类为托洛茨基的追随者,两方势力水火不容;再比如多伊彻的托洛茨基传记《先知三部曲》断言伏龙芝是季诺维也夫的门徒。仅凭我对伏龙芝的了解,以上两种说法都是纯粹的无稽之谈。
图哈切夫斯基和伏龙芝的关系是怎样的?图哈切夫斯基自述(可以直接看站内的翻译)与伏龙芝初次相遇于某次军事活动之中,他作为一个专业出身的统帅,对伏龙芝的军事才能做出了符合专业眼光的分析,给予高度认可和钦佩;加姆布尔格的《伏龙芝传》当中则写道,伏龙芝与图哈切夫斯基在军事上合作得很顺利,但是两人毕竟在不同的战线上活动,因此在合作之后处于长期分离的状态,直到伏龙芝成为红军第一人之后才发生了变化:伏龙芝请求中央将图哈切夫斯基任命为他的亲密助手。总而言之,图哈切夫斯基和伏龙芝是友好的同事关系,且这种关系基于实用的军事才能。
1924-1925年的苏联政坛的确存在派系斗争,但伏龙芝的所有军事行为都不是为了帮助某一派别政斗夺权,只是做了最符合军事需求的实用安排。多伊彻断言伏龙芝追随季诺维也夫,实际上完全找不到证据,而且很容易反驳,伏龙芝论政治资历是1904年入党追随列宁的老布尔什维克,论威望是在领导工人运动、指挥内战的过程当中真刀真枪打造出来的,季诺维也夫在军队中几乎没有任何影响力,内战中也缺乏光彩,不存在让伏龙芝追随他的机缘。非要谈论政治派别的话,不如说伏龙芝凭靠内战中的威望和能力,自己是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之外独立的存在,然后图哈切夫斯基是伏龙芝派。
但是
读过这篇小说之后,读者很容易同情主人公的命运,质疑机械主义的正确性,对政治阴谋感到厌恶,但是也应注意到,作者完全没有提及了“不折腰的人”为什么要动用政治阴谋迫害同事。当时的政治生态真的像小说塑造的那样不可直视不可言说吗?皮利尼亚克通过创造加弗里洛夫这个角色表达出了作者的个人理解,可是这足够覆盖伏龙芝本人的实际情况吗?换言之,前言中的解读对伏龙芝来说足够公正吗?
总而言之……这篇恶政隐文学其实非常适合当成一百年后的二次元同人小说来看待??小说本身不是独立的初创作品,必须要结合很多外部信息来读。作者将外部复杂的政治事件简化成了一个真人玩家——NPC和世界boss二元对立色彩很重的故事,注重角色的心理,在情绪上富有感染力(反复阅读故事很多遍甚至写了同人黄文之后还是在写加弗里洛夫遗书那段把自己看哭了),在行文上特别容易阅读和传播,反思机械主义的弊病存在一定的现实批判意义,但是怜爱、凝视加弗里洛夫的私人审美价值和朴素人文关怀属性凌驾于纪实功能之上,而且有男同。作为恶政隐文学,情感的浓度实在是漫溢出来了。作者是传统的主角嬷同人男。
让我们尝试从头了解那个传说故事背后曾活过的人吧:
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伏龙芝(1885-1925)是苏联初期党务和国务活动家、军事指挥和军事理论家,苏联武装力量的积极组织者和创建者之一。出身吉尔吉斯的医生家庭;1904年就学于圣彼得堡,加入苏联共产党;1905年起在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和舒亚组织工人运动。1907年被捕入狱,当局违反一般司法程序两次尝试判处死刑,服苦役直至1914年改判终身流放西伯利亚,后在流放地越狱,1916年逃回东欧一带组织地下革命工作,1917年十月革命期间带领工人和士兵队伍参与了武装起义。1918年正式加入军队,接连攻克高尔察克、布哈拉埃米尔和弗兰格尔等敌对势力。内战结束后在乌克兰地方统帅部队,期间参与了对土耳其的外交活动,1924年就任苏联陆海军人民委员副职并兼任工农红军军事学院院长,1925年取代托洛茨基转为正职。主导了1924-1925年军事改革,开创苏联军事学说。
皮利尼亚克给主人公起了这样一个名字,本就体现了该角色和现实中伏龙芝之间存在着强烈的对应、混同关系。“加弗里洛夫”词源是圣经中的天使长加百列,和伏龙芝的名字“米哈伊尔”的原型米迦勒相照应。波波夫和现实中具体人物的对应关系较为薄弱,不是为了在文学中影射现实人物,更像是作者对加弗里洛夫的人文关怀的化身,依附加弗里洛夫而存在。尽管波波夫和加弗里洛夫都不过是常见的俄国姓氏,此处姑且还是将现实因素综合考虑进来:伏龙芝的妹妹克拉芙季娅婚后随夫改姓加弗里洛娃;伏龙芝的妻子索菲亚·阿列克谢耶芙娜婚前姓波波娃。